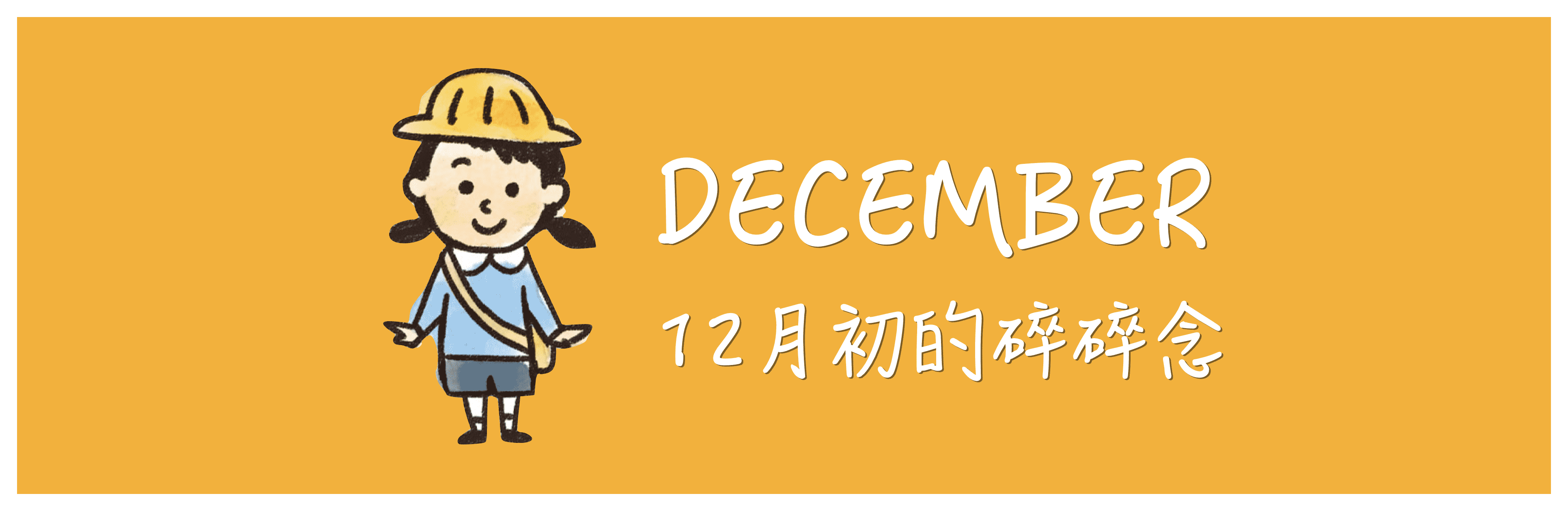
星期四那天上午,我结束了大学里的最后一节课。从某个角度而言,我的大学已经结束了。然后我回到工作室,吃饭、学习,仿佛一切都还没什么变化。
星期五我去了工作室答辩现场,评优只有三等奖。作为过去这一年里焦糖的打工人之一,我发现我也有了老父亲心态:其实工作室title什么的都没那么重要,只希望大家最后都能去到想去的地方,做自己想做的事。 不过细想,我们这届活跃的人里,99%都已经拿到了一线厂的offer,只有自己还在挣扎。发现自己不过是在操无关紧要的心,就自认为很好笑。
然后我就回寝室收拾行李,回家了。
下地铁口的时候,我突然想到,2020这一年我真的做了好多好多事。 一月份我写了人生中第一封套瓷信。它实在是简陋破碎,却也竟被善良的人捡了起来。四月我完成了人生周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论文,而在六月我就收到了人生中第一封接收消息。幸福感实在来得太快,那时候我还来不及思考,就被节奏带着向前行走,仿佛看见了一个光明的未来。
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,逆流向上的小舟,不停地倒退,进入过去。[1]
然而幸福没有持续多久,当我花了大量时间跑实验却没有理想效果的时候;我开始怀疑,自己是否适合科研,自己做的这一切是否是有意义的。 然后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,寻找做这些事的意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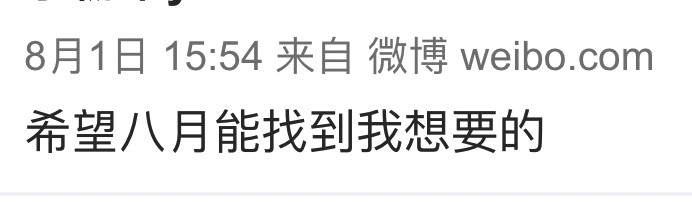 最后,我得出的结论是:
最后,我得出的结论是:
对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而言,没有任何意义。
可是,当个体面对人类群体、面对宇宙时,本来就如此渺小。从宇宙大爆炸、到生命大爆发,直到21世纪今天,自然科学从未被我们找到解释依据。人类为自己、为世界构建了一个一个理论,也永远无法超越生命最基本的样子。
或许,宏大叙事的意义本就没那么重要。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说,人存在的意义无法经由理性思考而得到答案。那么,我又如何认可自我对自己的价值和意义?我怎样寻找到“自己”对自己的重要性?
我总是会想,自己不够强大、不够温柔、不够好看、不够有趣,一切和美好相关的词语都跟我沾不上太多关系。 我想起了我喜欢的那个男生。不喜欢我的他也仍然是美好的,美好之所以成为美好,大抵也是因为我可望不可即罢。
我总是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。 星期二晚上全年级都在问,去T大NLP的那个人是谁。嵌入式专业群甚至有匿名call我。于是我在群里生气。而匿名只是说:“何必戾气这么大呢。”那时候我由衷的觉得,人和人之间永远是没办法感同身受的,这社会也本就不是靠人的相互理解而运作的。
后来我的理智说,那又怎么样呢。别人的看法的评判真的有那么重要吗?我只需要过好我自己。为自己做不到而难过、为自己求而不得而痛苦。
半个多月前,那时我还面临着转方向、没offer、被喜欢的人拒绝等一系列的糟心事。我问工作室学长:我一定要为了升学而考虑明年的去向吗?我怕即使我找到了好的RA,最后也保不了研,或者也只能保本校。
问出口的时候我就知晓了,现在的我只是想找个地方继续做研究,找到我想要为之奋斗的事而已。关于深造、关于学历,那些好像都还很遥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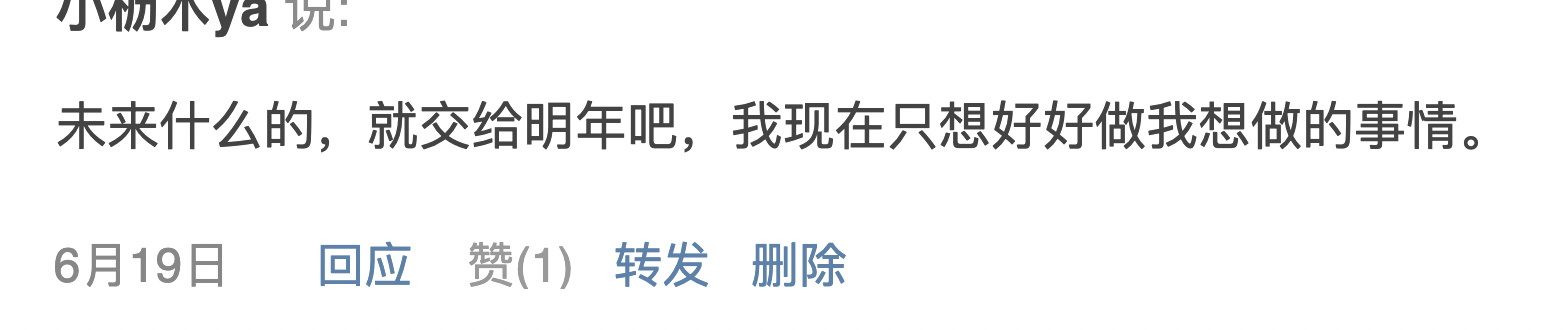
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里写到:
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,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;它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,朝向其他自由,才能实现自由;除了向无限开放的未来扩张,没有其他为当下存在辩解的方法。[2]
作为存在主义也是自由女性主义最初的代表,波伏娃提倡以超越性来实现自我价值。人的行动并不依赖于其意义,跟语言中的概念一样,维特根斯坦说,“语言的使用并不依赖指示具体‘物’的‘意义’(Bedeutung),而是一种‘语言游戏’”[3]。人生也是一场游戏,一场“有规则”的游戏,拥有乐趣、目的、不受约束的变化性;不受“自然”的因果束缚,而受人的“自由”的规范约束。
自由是生命中永恒的命题,不断追寻自己所想,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。
I am flawed if I’m not free. [4]
[1] 菲茨杰拉德, 姚乃强(译), 了不起的盖茨比, 2004-06, ISBN: 9787020046089 [2] 西蒙·波伏娃, 郑克鲁(译), 第二性, 2014-1, ISBN: 9787532763399 [3] 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,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, 2005-05, ISBN: 9787208054707 [4] Rilo Kiley, Does he love you?, More Adventurous, 2004